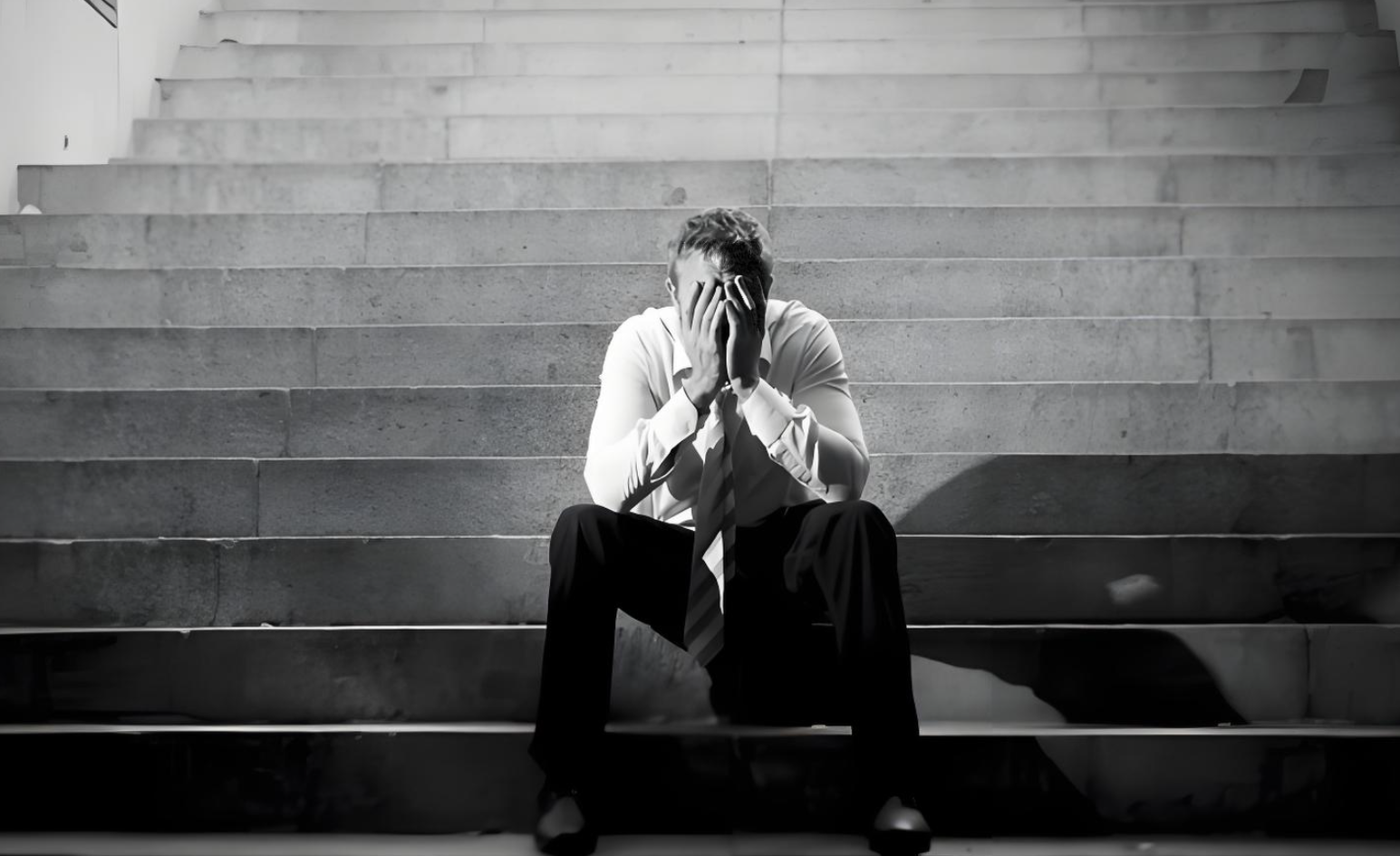
中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已达39.1岁,夹在日本的49岁与越南的32.4岁之间。从人口结构来看,中国正式迈入“中年国家”行列。相比之下,日本是“深老龄社会”的样本,而越南则代表着“年轻国家”的活力象征。
为何要将三国放在一起分析?不仅因为地缘相近,更因其发展路径皆以“出口导向+制造业崛起”为核心。中国继日本之后坐上“世界第二”宝座,也同样面临来自“世界第一”的结构性阻击。在这个位置上,日本曾辉煌也曾迷失,如今,中国也进入了关键拐点。
而越南——虽体量尚小,但其近年来的经济跃迁与体制改革,被视为“迷你版中国”,其政策动作,正成为改革对照样本。
中国地方债问题长期被聚焦,但从日本的“高负债+高保障”模式来看,债务并非原罪,关键在于花得值不值。
日本虽然GDP增速长期偏低,但就业稳定、治安良好、社会保障覆盖广泛,其净资产和家庭财富近年均创历史新高。换句话说,日本走的是“慢增长+稳保障”的模式,核心支点就是财政长期负担下的高水平社保。
对于中国而言,这种模式背后最值得借鉴的,是“结构性负债逻辑”:
1、好债务,不是建空城,而是投资人本身: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住房保障等。
2、可信债务,是能够偿还、有责任感的负债机制。
3、可持续债务,是确保财政可以持续供血、不崩盘的制度设计。
我们过往强调“要想富先修路”,如今应进化为“要想强,先育人”。若将未来几十年的社会保障和民生建设看作国家“长期人本投资”,那么中国需要的是更聪明、更精准、更责任导向的“新负债观”。
越南改革的最大亮点并非经济数据本身,而是其“自上而下”的结构性改革决心。
1、省级行政区重组:从63个缩减至34个,相当于以一国之力做“省改市、县合并”。
2、政府精简与职能转移:更重效率、更小规模。
3、政务运作全面数字化:压缩中间成本。
对比之下,中国同样具备改革需求,但国情不同,路径不能简单照搬。但“精兵简政、优化结构、下放权力”绝不是空谈。
当前,国内已有90个“袖珍县”,人口不足5万,财政严重依赖转移支付。对于这类区域,调整机构、合并职能、资源整合,是推进地方政府瘦身的必经之路。
此外,中央已在2023年启动“5%编制精减”,这类渐进式改革,若能扩大到地方财政、社保及营商环境领域,将真正触达“改革的效率阈值”。
想实现更高水平、更广覆盖的社保,单靠政府显然不现实。
以年金制度为例:
1、职业年金(机关单位)覆盖率接近100%,且为强制缴纳;
2、企业年金覆盖率不足6%,其中民企更低于3%。
这种结构性不平等,若长期存在,未来将带来巨大养老代际冲突。
而日本的做法是:“政府兜底+企业参与+个人共担”,通过提高延迟退休灵活度、逐步拉高税率(如消费税)、推行“高收入老年人多缴多付”等手段,建立起较为平衡的社保体系。
中国也要尽早走出“政府包打天下”的思维误区,在政策上提供税收减免、财政激励,引导企业尤其是中小民企加入社保体系。
中国正站在“中流”之上,左右是浪,前方是急。这个时代,不是最轻松的时代,也未必是最危险的时代,而是——决定方向的时代。
毛泽东在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说:“到中流击水,浪遏飞舟。”
这句话放到今天,仍适用。“中年中国”不是停滞期,而是选择期,是调整期,更是转型期。该做的,不是纠结速度放缓,而是更精准地“用好债务、推好改革、调好结构、做实民生”。
未来的中国,是一个能持续激发社会活力、不断修复代际不平等、并具备风险应对韧性的国家。
也许,这正是“中年国家”真正成熟的标志。
 百度热点
百度热点
 抖音热榜
抖音热榜
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
 今日头条
今日头条
 腾讯新闻
腾讯新闻
 知乎热搜
知乎热搜
 36氪
36氪
 雪球网
雪球网









